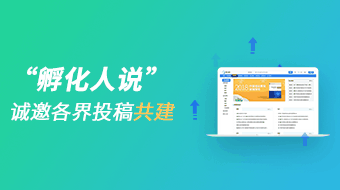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,孵化器具有二重属性:既是政策工具,又是营利手段。
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的出现,纯属偶然,那是1959年贝特维亚小镇上的一个故事。但当上世界八十年代各国政府、社团、大学等等开始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推广孵化器模式的时候,孵化器被当作很好的政策工具,而在2000年前后,孵化器的营利属性开始显现。
我接触到最早关于政策工具的阐述,是R.拉卡卡先生的。1996年,天津创业中心组织翻译他的著作,《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孵化器》(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,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,1997)。其中比较了支持创业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类型的政策、措施,结论是:孵化器是物美价廉的政策工具。我那时参与了一点点这个工作,校了一稿,记得很清楚的,初译中,常常把孵化器的单位译作“座”或者“台”,真的是把孵化器当作一种设备了。
孵化器作为政策工具,可以用来扶持特定人群、改善区域经济结构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、支持特定产业等等。在这方面,我看,中国是做得最好的,以色列其次。
中国在引进孵化器这种模式之初,就把它当作“发展高科技,实现产业化”的利器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的孵化器基本上都是科技型的,即只孵化培育科技企业。三十年来,孵化器一直是民营企业生长的摇篮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又利用孵化器来扶持留学归国人员创业。也曾经在天津出现过支持妇女创业的孵化器。
其实,作为政策工具,孵化器的能量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,即使在“双创”潮中,用途也还是比较狭窄。未来,在孵化、扶持新生产业和幼稚产业,以及支持特定人群等方面,孵化器定会大展宏图。
孵化器作为营利手段受到关注,始于2000年前后。在互联网热潮中,美国一批营利型孵化器推波助澜,小批量、短时间、深度地大规模地注入资源,让创业过程变得非常短促,让孵化器的盈利非常显著。就是在那个时候,美国人把这类孵化器称做加速器。Idea lab!是一个典型,李开复先生创办的创新工场,大致是将其作为原型。
第一次互联网泡沫之后,这类孵化器遭受打击,但很快恢复过来。现在比较活跃的美国的YC、德国的Rocket等等,盈利能力都很强。
中国的营利型孵化器产生于本世纪初,民营的孵化器,一上来就是营利性的,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孵化器行业的结构和形态。
我考虑,孵化器这样的二重性,或者换个表述,社会性和经济性,是天然的。这两面是相对立的,以哪一面为追求目标,决定了一个机构的属性、样式、绩效;在很多情况下,两者又是同一的,有了好的经济效益,才能有好的经济效益。
认识、思考孵化器的二重性,对于政策制订者、孵化器投资者和经营者,都是很有必要的。